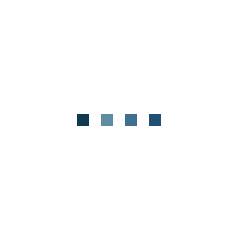國三那年,爸爸在大陸包二奶,跟媽媽離婚。媽媽要我出人頭地的壓力更大了。某個假日,我讀書讀到累了,跟媽媽說要休息,她大罵:「休息什麼?考試要到了,給我去補習班好好讀書。」走進教室一看,大家都跑去玩了,只有我一個人。我把書丟進垃圾筒,癱在桌上大哭。
我沒考上好高中,只好讀職校。我不知道自己已經得了憂鬱症,注意力無法集中,腦袋鈍鈍的,言語表達也不正常。我沒有求援,反而說服自己只是欠操,應該要給更大壓力把自己拉上來。直到有一次在課堂自習時,我忽然大吼大叫,亂摔東西,老師才把我帶去精神科就診。媽媽忙工作,沒有來,回家才跟我說:「有心事要講喔。」從小我不曾體會愛,也不懂得要怎麼表達感情,我什麼也沒說。
大學某一天,我在客廳看電視,媽媽突然開口:「以前那樣對你,會不會恨媽媽?」我覺得好彆扭,只能敷衍說:「沒有,沒有。」坦白說,一句道歉救贖不了我的創傷,反而像在演八點檔,太做作了。
幾年前我進了精神病院。那裡沒有手機也沒電腦,環境單純,我好像忽然獲得喘息,藥物讓我血清素提高,變得心情愉悅,每天大量閱讀、做體能訓練。我後來把壓力都發洩在體能鍛鍊上,比如伏地挺身一次做一、二百個,在地板上寫一個忍字,撐很久,我大概是從小被控制久了,受虐變成了自虐,自我規訓讓我覺得自己變得有價值。
出院了,我考取健身教練證照,和朋友合資開健身房。健身的過程很像人生,必須用力摧殘,經歷痠痛,才能重新長出肌肉。某方面,我算是「好」了吧。但是我對媽媽糾葛了好多複雜的情緒,一看到媽媽就會打回原形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少回家,我只能住在健身房的休息室裡。
于郅弘 30歲 台北市 健身教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