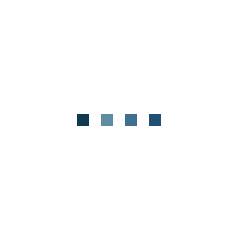「我在台灣拍藝術片居多,來香港才學拍動作片,動作片攝影師要跟演員一起武打,但沒人教我,如何手拿機器快速移動又不抖。試戲時我仔細看,發現用小碎步跟拍,比較不抖。香港很現實,我沒地緣也沒人際關係,萬一被換掉,路就斷了,於是我壓迫自己一定要超越自己,一次都不能失誤。人生有時候連一次都不能錯,錯了就再也回不來。」
那年代港台不太互通,獨在異鄉為異客,很是孤獨。「那種失落感,讓我常常不想起床,一起床就要面對今天,很不想去現場,現場沒一天好過。其實很矛盾,我希望人家找我拍片,但沒有導演是請你去輕輕鬆鬆交朋友,他們是要你拚命啊!」
尋光影 找麻煩求生
為了精進美學造詣,他靠欣賞國畫大師李可染、傅抱石的水墨畫,以及收藏古董瓷器來「養眼」。水墨畫以黑白表現情緒,明暗刻劃細節,瓷器有精緻又考究的工藝線條,耳濡目染久了,上乘的光影和花色會主動打招呼。「這對我影響在哪?有時候拍東西只拍一個大氛圍,容易忽略細節,所以我也渴望追求這種細節。我把這套技術挪用到攝影,一開始,很多人覺得我是外行人,嫌我不懂光,又不懂得用燈,其實我有用,只是把黑也運用在其中。」
在教養院養成獨立早熟的性格,在香港搏命求生培育出處變不驚的意志力,至今,他仍不斷給自己出難題,從嚴苛裡求新求變,比如用日光片拍夜景、挑戰失焦鏡頭,或把傳統濾鏡層層加疊,配出新顏色。

「2000年左右,很多學生畢業以後說沒錢、沒設備,我就跟侯導說不用專業的燈,看可不可以拍?我們用日光燈,60瓦、100瓦的燈泡也拍了3、4部電影,從《千禧曼波》到《紅氣球》吧。那時也是一種挑戰,我們已經很少燈,為什麼還有人說他們器材不夠?這也是一種激發,在激發裡面就會產生一種不一樣的鬥志跟呈現。」這種自找麻煩的性格,很像是俠客中的「獨孤求敗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