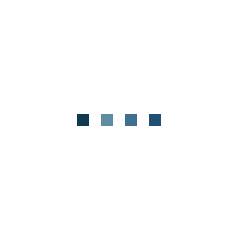楊索也採訪許多底層的人,「我會很入戲地聽故事,要有那個真誠才能感動他們,讓他們願意講。可是那個東西會留在我心裡。」有一回,她採訪遊民製作頭版專題,跟受訪者在平安居(收容所)住了3天。刊出後,遊民勃然大怒,不希望家人知道他落魄。楊索也問自己,她究竟有何資格掀開別人的傷口?連續好幾天,她不敢接受訪者電話,也體悟到報導無益於改善弱勢族群的困境。
「我回家已經是深夜了,那個情緒像一口井,水都要滿了,我開始寫第一篇文章。寫到天亮, 回頭張望我在菜市場長大的日子,寫的時候像剝洋蔥。」直到這時,楊索才開始寫自己的故事,在記憶中重返那個破碎的家庭,她的祖父就是別人眼中的遊民,流浪是她從小就熟悉的命運。

楊索和小妹都記得,小時候要輪流看守祖父,因為祖父總會失蹤,找回來時滿身皮膚病,回想起來應是早發性失智。楊索話鋒一轉,驕傲地說,祖父雖然不識字,卻可以唱出優美的四句聯,像希臘的吟遊詩人,她到現在還記得幾首,準備背給我們聽時,她忽然泣不成聲,可能是喚起了她失學的悲哀,或是命運的淒涼。沉默了許久,弟弟銀色快手代替楊索緩緩道出:「聽姊姊說,祖父沒有念過書,又被村子視為奇怪的人,可是會去廟裡借書來讀。」
不單是楊索和銀色快手走上寫作的路。三弟也問過楊索,假如他寫文章,報紙會用嗎?當時楊索回答:「好啊!那我們家就有兩個人想當作家。」後來三弟開設部落格。小妹也常逛書店,某天默默買了楊索的書,終於了解過去的事。
一個沒有機會說出自己故事的靈魂,儘管忘了回家的路,也忘了自己的名字,但他還是留下了許多愛書惜字的孫輩。